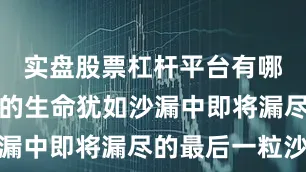抗战时期,河源民众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抗敌斗争,其行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微观缩影,印证了“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”的历史进程中,普通民众始终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力量,也凸显了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的凝聚力与抗争精神。
自河源县成立御侮救亡分会后,面对外寇煎迫、民族生存,抗战即将开始的局势,各界加紧抗日宣传,以期唤醒民众共纾国难。在捐输助国方面,形成了“行业联动、乡土凝聚、党群协同”的特点,既依托宗族、商会、学校等组织网络,又融入当时地方政府、中共党组织的引领,展现了抗日战争中“地不分南北、人不分老幼”的全民抗战精神,为前线御侮提供了持续的物质与精神支撑。
在投军与军训方面,从现存各类报刊报道资料看,既有乡绅、壮丁依托地方组织开展的军事化训练,也有学生群体突破年龄限制、主动请缨的热血行动,更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(如大刀术)以适应战场需求,充分体现了河源民众踊跃投身抗敌的决心。
展开剩余88%具振中等多人发起并签名的《为促成全县精诚团结抗敌救亡宣言》。
01
全民总动员,捐输救国难
早在全面抗战爆发(1937年)前5年,河源民众就已经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行动。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,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,1932年一·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,和平籍将士出征浴血奋战的消息传至河源,民众迅速觉醒,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,抗日情绪高涨。各界“为正常防卫,未雨绸缪计”,采取了募捐、宣传抗日、抵制日货等行动,行动覆盖学界、商界乃至普通民众,抗日已成为河源地区各界的共识,形成跨阶层的抗日合力,呈现出全民抗战的雏形。
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河源支会公函
1932年2月,河源学界方面,中小学校组织募捐队12支,向各机关及绅商富翁募捐。另由各校组织宣传队15支,不分昼夜,在城市街道,及周边乡村宣传抗日。商店方面,一致决定不买卖日货,如果发现罚百金。各店门头,自动张贴长标语一张,有的写着“如买卖日货,便男盗女娼”等字。
这次的抗日行动,不仅为后续全面抗战中的捐输助国(如1937年商会倡议、1938年献金运动等)奠定了社会基础,更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非始于全面抗战,而是在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过程中,逐步积累力量、凝聚共识,展现了持久抗战的群众根基。
1937年七七事变后,河源再度各界联动、全民参与御侮救亡,学界、商界、城市居民、乡村与宗族、中共党组织与妇女群体等一起形成合力,多元化捐输助国。
8月1日,河源县商会倡议捐输助国,以助我军御侮救亡。9月23日,河源县商会召集各行商代表开会,讨论慰劳空军办法,结果各商店愿将全日膳费捐出,以慰劳空军将士。此外,河源县属各区乡村居民,多世代聚族而居,且设有蒸尝(宗族公共财产),每年收入甚丰,作为祭祀之用。二区坪山等各乡民,鉴于国难严重,无国即无家之义,倡议发起由各族捐蒸尝款救国,将宗族资源转化为抗战资金,获得广泛赞同。1938年5月9日,河源县府派员劝募、催缴附城之联安、三社、义荣三镇国防公债。
1938年,蓝口镇公所劝募镇内商号缴交救国公债款,天和号商铺多次捐款抗战。
1938年4月,河源县商会发起“节食运动”,每月农历初五、十五、廿五改食杂粮,将节省的开支用于救国;1938年8月,河源县献金运动委员会发动4天献金,附城收到现款2000多元。商家不仅捐现金,还主动捐献店铺、田产——1938年8月,县民江济平、江子坤、谢滋生各献田一块,邹道存献店一间(价值600余元),由献金运动委员会拍卖后充作抗战经费。乡镇的商家亦与县城商家一道捐献,蓝口镇天和号商铺多次捐款抗战,镇公所主动劝募商号缴纳救国公债款。
1941年防空节,在城镇公所、布疋同业公会、京药同业工会等乡镇组织与行业团体,均以集体名义献金(5元至10元不等)。这年的防空节,国民党河源县党部通过“义卖”献金241元,以创新形式扩大捐输规模。
1938年5月上旬,崇伊中学战时服务团自成立后即加紧训练各组人员,并派遣宣传、募集两组人员80多名,实行宣传、募集工作,募集资金300元以上,悉数汇往武汉军委会。
同年7月,中共蓝塘特别支部以“抗敌后援会”名义,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活动中募集钱物折值白银5000元,送至八路军广州办事处。曾担任中共惠紫河博特区委组织委员的郑策元,在抗战期间于香港开设“万光兴汇兑庄”,专门筹款支持抗日。
1941年防空节,第四区专员公署、县政府、税务局等机关集体献金,捐出5元至100元不等;县长、法官、校长等公职人员以个人名义捐款,商家、各机构及市民均踊跃参与。1941年11月24日的《河源民国日报》将献金者名字及金额一一公布:第四区专员公署50元,第四区党务督导处10元,国民党河源县党部领导义卖献金241元,国民党河源县党部10元,河源县政府68元,河源税务局20元,河源田赋管理处50元,河源县国民兵团55元,河源地方法院15元,河源查验站50元,省银行办事处30元,钨业粤二所10元,河源税捐征收处10元,河源县商会10元,河源圣心小学100元,河源县立中学15元,附城镇中心学校20元,在城镇中心学校10元,警察所10元,政警中队部□元,县妇女会□元,乐育小学10元,在城镇公所5元,布疋同业公会5元,京药同业工会5元,平码同业工会5元,河源卫生院2元,盐糖同业公会2元,童镇长慎君10元,陈日东先生10元,于庆鹏先生5元。
此外,1937年10月,《河源日报》刊登启事,向社会征集军毯、棉被、伤兵衣物(灰棉布衣裤、灰单衣裤、白衬衣裤、灰布帽、新旧棉花胎、厚棉绒手套手帕、草黄色咖啡布衬衫、白色或草绿色短裤、拖鞋)、药品(药水棉花、纱布)、手电筒(永福牌电池电泡)等前线急需物资,学界积极参与动员,将募捐范围从资金扩展到实物,直接支援伤兵救治与将士补给。
02
抗日歌声响彻街头,学生演剧唤醒民众
抗日战争时期,河源各界为唤起民众爱国热情、支持抗战,在宣传和巡游方面行动采取了多种措施。
先是召开抗日集会,凝聚抗敌共识。1937年6月27日,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河源各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,以此督促政府领导民众,扩大民族生存斗争。国民党河源县党部、县政府官员、军队代表、学生、机关团体代表等800多人参会。通过报告开会意义、演讲抗战理由等形式,营造浓厚抗日氛围。会后,人们高呼口号,继续巡行。由会场出发,经飞鸾桥入新东门,又到县前街、北直街、化龙路、太平路。沿途派发各种宣传品,高呼口号,至第二市场散队。
各地民众成立了多种宣传团体,开展多形式宣传。1937年9月,中共党员潘祖岳以县立二小师生为基础,吸收爱国人士成立蓝塘大众救国团及教师联合会、学生联合会等;1938年,河源县中学生组织第一宣传工作团,崇伊中学成立战时服务团;1939年进步学生和爱国志士组成抗日宣传队等。
宣传队分赴各区乡、乡村开展工作,如河源县立中学学生宣传队分4队前往不同区域农村;中共党员张华基、丘国章、刘成章等在黄村组织抗日宣传小组,深入县城和农村;流亡的广州艺协剧团到河源、老隆等地演出戏剧、歌咏,协助组织民众。
他们采用的宣传形式多样化,包括演讲(讲述国耻史实、兵役利益等)、街头剧表演(如县中附小在太平路口表演,围观者众多)、演出抗日剧目(如《死亡线上》《送郎当兵》《还我河山》等)、高唱抗日歌曲(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流亡曲》)、派发宣传品等。1938年5月6日为河源圩期,县抗敌后援会连日派出化装宣传队作演出、演讲。第一宣传工作团出发本地繁盛地点宣传抗战,沿途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,听者百余人,无不动容。该团是县中学生组织,团长谢荣光。附小各导师详细讲述国耻史实,及充当兵役之利益。县相关机关会同组织抗日宣传队,分赴各区乡加紧宣传,并作有定期演讲。
为达到良好宣传效果,相关机构建设了部分宣传设施,保障宣传开展。1937年8月中旬,河源县民众教育馆在新城附近新街旷地建筑抗日宣传演讲纪念台,所需约500元资金由各界机关团体捐资,为抗日宣传提供固定场所。
在宣传队的表演感染下,民众时常慷慨捐款。1939年,河源抗先队流动宣传队通过街头剧等形式引发民众共鸣,收到的捐款被送往难民收容所。
03
河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
抗战期间,河源各地成立各种协会,如民众抗敌后援会、御侮救亡分会等。
河源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:1937年8月成立。
龙川县民众抗敌后援会:1937年10月成立,主要发动民众捐输钱粮支援抗战。
河源县御侮救亡分会:1937年11月前成立,负责仇货登记、组织检查队检查仇货等工作。
河源县民众抗日自卫团:1937年11月成立,下设32个大队、7个独立中队,约1.7万人。
紫金县御倭救亡会(后改名抗敌援救会):1937年7月上旬成立,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
和平县抗敌后援会:七七事变爆发后成立,1938年县长李则谋出任主任,该会还举办“和平县战时干部训练班”等。同时,和平县各乡镇成立“抗日后援会”。
和平县各界“抗日同志会”:在和平县抗敌后援会推动下成立的抗日民众团体组织。
广东省青年文化研究社和平分社: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和平音乐剧社: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和中剧团:由和平中学师生与从上海、广州返县的青年师生组织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奔流剧团: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黎明剧团:抗战时期在和平大坝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晨钟剧社:抗战时期在和平县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岑岗夜鹰歌舞团:抗战时期在和平岑岗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林寨新生剧社:抗战时期在和平林寨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彭寨联中剧团:抗战时期在和平彭寨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下车浰东剧团:抗战时期在和平下车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04
“这里是全民皆兵”
抗战时期,河源民众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踊跃投军并自发开展军训。从现存各类报刊报道资料看,既有乡绅、壮丁依托地方组织开展的军事化训练,也有学生群体突破年龄限制、主动请缨的热血行动,更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(如大刀术)以适应战场需求。这些行动既反映了全民抗战背景下的自发动员,也为后续正规军补充和地方防御奠定了基础,是河源民众“御侮救亡”决心的直接体现。
早在1932年2月,日本侵略消息传至河源后,柏埔、白田、埔前、高埔、石坝、黄麻陂、石峡、七火金等地迅速响应,纷纷组建义勇军,聘请退职军官担任指挥,开展“野战工作”训练,目标是“练成劲旅,与日军作殊死作战”。其中柏埔、石坝、石峡、黄麻陂等地的义勇军已完成组队,形成基层抗日武装力量。
河源上游新丰江一带乡民,对国术的训练非常勤快,武风异常旺盛。1937年8月,乡民因受“抗敌救亡风气”影响,结合华北战场“大刀杀敌”的经验,由各乡武术教师召集乡中学徒、壮丁,专门改习大刀,使普通乡民掌握近战技能,为“同赴前线杀敌”做准备。为避免训练被误会,武术社教师龙祥还呈请河源县府布告保护,确保训练顺利开展。
河源各地学生亦纷纷投笔从戎,主动请缨杀敌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龙川县各界群众集会示威,龙川中学学生“自发军训,请缨杀敌”,将课堂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,主动要求奔赴前线。1937年8月,驻河源四路军干调处招考学生时,崇伊学校学生欧阳国鉴、韩辉庭、张思玲(年仅11岁)等6人,因“忿日寇之无理”,毅然投笔从戎。他们仅携1元船费,欠缴部分由东江药房代付,抵达河源投考。虽因“需18岁以上”的规定受阻,但“志切从军,到前线杀敌”的决心令人动容,展现了青年学生的抗敌热忱。
资料来源: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香港工商日报》《天光报》《河源民国日报》《河源日报》(民国)《香港华字日报》《河源县志》《紫金县志》等。
发布于:北京市悦来网配资-配资炒股app最新版本-配资交易软件-民间配资盘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